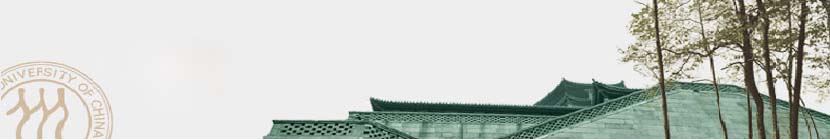胡绳武:生于1923年,著名历史学家,祖籍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夹坊村。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地系后留系任教。1962年至1964年借调教育部编写教材《史学概论》;1974年借调《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75年调入国家文物局,先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古文献研究室负责人;1980年进入新莆京app下载官网清史研究室工作。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新莆京app下载官网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颇丰。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的著名专家金冲及教授进行长期合作,著有多部专著。
动荡年代辗转求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胡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我注意到您大学时读的是史地系。您是如何选择史地系的,能回忆一下当年的学习生活吗?
胡绳武:我选择史地系是因为比较喜欢这个学科。我的老家是山东枣庄,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台儿庄大战就是在我家门口打的,后来沦陷了,我一度因此失学。之后又克服困难,去济南继续上学。
七七事变后,山东省流亡到四川的几所中学联合在四川绵阳成立了一所国立第六中学。我们在济南念书时得知了这一消息,就决心去国立第六中学读书。1943年春,我们三个同学一起从沦陷区去绵阳,三人顺利进入国立六中高中部学习。有几个学者,如后来做宋史、现在已过世的漆侠,当时就是我六中的同届同学,他在十级2班,我在十级3班。还有十级4班的戚其章,也是我同学,他后来成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专家。当时一共四个班,一个班三十几个人。我和戚其章的交往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他每次出书都会送我。
到1944年5月,我们毕业班的同学都想考大学,因为考上大学除了能进一步深造外,还可以享受公费待遇。中学毕业时,最有办法的,就是成绩好又能筹出旅费的同学,他们优先选择去昆明考西南联大,其次是到成都考川大,或者去重庆考中大。最没办法的同学就步行120里路从绵阳到三台考东北大学。我当时属于后者。后来,在复旦读书的六中校友来信,在学校墙报上介绍复旦大学的情况,说复旦风景多么的好,欢迎六中校友报考,于是我出于个人兴趣,决定报考复旦大学史地系。当时考史地系的目标是做一个中学教师,根本没想到会留在大学工作。
1944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在重庆和上海分别读了两年。在重庆时,学校在嘉陵江边,对面就是北碚风景区,很漂亮。那时候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学生课余时间很多,不像现在学生课业那么重。学校社团也比较多,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各种社团活动,我主要参加了“时事论坛报”的活动。当时的考试非常严格,复旦考试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一排是学史地,挨着的是学哲学的,另一边是学经济的,根本不可能作弊。如果英语考试有两年不及格,就除名,蛮严格的。新中国成立后学苏联,一个星期三十几堂课,学生课业负担就变重了。
当时大学师生间的关系非常融洽。除了史地专业,我还去听新闻和中文专业的课,与其他专业的老师非常熟,常到他们家中聊天。我还记得,顾颉刚先生在复旦大学兼课时,我上过他两门课 历史地理和春秋战国史。他口才不是很好,但粉笔字写得很漂亮。我们在重庆和上海时交往比较多。后来我来了北京,交往就变少了。
历史研究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国内较早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著名专家之一。《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就刊发了您与金冲及先生合作的《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一文,是哪些原因促使您选择研究辛亥革命史的?
胡绳武:我研究辛亥革命史是从教中国近代史开始的。1948年我毕业时,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留校当助教。本来中国通史应该由助教林同奇教,但他哥哥林同济办了一个海光图书馆,他就去图书馆做研究员了,中国通史就没有人教了,他推荐了我,于是我一毕业就教中国通史,带4个班,压力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去教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之后又教马列主义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17所大学合并到复旦。之前复旦只有8个教授,合并后一下就有了16个。当时学苏联,增加了近代史专业课,但大家都不认为近代史是一门学问,16个教授没有人愿意教,后来就安排我去。我说我教不了近代史。后来中国近代史变成一门基础课,经过研究决定让陈守实教授教,他理论基础好,让我辅导。半年后我开始教近代史,自然就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就这样,我从1950年代就开始研究辛亥革命史了。
一开始,我把研究重点放在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和复杂。弄清这一段复杂历史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特别有意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20世纪50 年代初大家还不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学问,当时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度非常不足,研究成果自然比较少,也存在许多值得花力气研究的空白点。因此,我选择了这一历史时段进行研究,并在《复旦学报》接连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是《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1955 年第2 期) 、《孙中山初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1957 年第1期)和《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1958 年第1 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还关注近代史的研究吗,对今天的近代史研究有何建议?
胡绳武:我年事已高,要继续深入研究近代史有一定难度。我认为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弱点在于对外国研究得太少,例如当时西方是如何看中国的,持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插手祺祥政变,有没有插手辛亥革命,特别是英国、日本,插没插手,是怎样插手的,在哪些问题上插手了,对这些问题,我们研究得还不够,对外国的报纸、档案等资料运用得还不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整个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老一辈的研究人员很少用外文资料,英语都丢掉了。不过现在好了,留学生多了,外文基础也好,可以在这方面多做点研究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除了在中国近代史方面颇有建树外,还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有研究成果,能谈谈这些方面的情况吗?
胡绳武:这与我1962年参与《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有关。这个编写工作持续了差不多两年,后来不了了之,但我在编写过程中写了两篇文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科学的任务》写了3万字,没有发表,后来弄丢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有5万多字,最初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动态》1981年第2期,到1984年才被四川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为写这两篇文章,我下了很大力气。在我看来,历史研究要成为科学,就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就需要弄清楚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要把这个形成过程弄清楚,就需要阅读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弄清楚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了解当时工人运动的情况。我不是学哲学的,要花很多功夫,但这些功夫,对于我后来研究辛亥革命非常有用。我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我的文章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遵照“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这一原则,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在今天,这些理论和方法依然有效。
携手完成《辛亥革命史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有不少重要论著是和金冲及先生合作的,能谈谈您与他交往的情况吗?
胡绳武:我和金冲及是同学。他比我小7岁,他进入复旦史地系读书时,我已经大学四年级了。当时系里学生少,我们很快就认识了,但交往并不多。1953年秋,复旦大学新闻系向历史系提出要开设一门每周3课时、为期一年的中国近代史课。那时我一周的课时比较多,没有办法再教,就推荐了金冲及。他当时是学校党委书记的秘书,也很乐意来兼课。
我们合作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 兼评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的若干论点》(《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但发表时,他把我的名字加上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学术观点是您在会议上讲过的嘛。”他把当年我在天朝田亩制度课堂讨论会上发表过的观点吸收到他的文章里,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合作。
后来我发表论文,也把他的名字加上了。例如,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文章虽然是我执笔,但我将他列为了第二作者。之后我写《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书的时候,也邀请他和我合作。
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一般谁执笔,谁的名字就在前,在发表前,彼此交换过意见,是相互认同的。合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我和金冲及这样合作的,很少很少。我们是同学,又在一个单位工作,经常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与金冲及先生合作的《辛亥革命史稿》1 4卷,和您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受到了学界好评,是代表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佳作,这些论著的史料都非常丰富和扎实,展现了您和他在占有、鉴别和分析史料方面的高超技巧。可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胡绳武:要搞清楚历史是比较难的。我当时将大量精力放在《辛亥革命史稿》上。这部书的第一卷是我和金冲及一人写一半,第二、三卷我写少数一部分,第四卷全部是我写的。尤其是第四卷,跨到民国初年了,这一段历史特别复杂,需要看大量的报纸。民国时期的报纸种类繁多,我在北京图书馆查了很多资料,尤其是报纸。我家就住在北图报库后边,很方便。我到人民大学教书后,课比较少,大量时间都在报库看报纸,尤其是为写该书的第四卷,我看了多种报刊,摘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仅查资料就用了三、四年。由于看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所以这部书的论述有可靠的史料做基础。
学术文章要用史实说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一些重要文章,又曾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过,能谈谈您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情况吗?明年是《历史研究》创刊60周年,您对于这份刊物未来的发展有何期待?
胡绳武:我是1974年7月到《历史研究》工作的。当时毛泽东主席批示要恢复《历史研究》的出版,并从13个省市调了23个人,除去后来回去的两个做历史地理的人,一共留下21个人。我来北京时,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因为当时我正在组织《沙俄侵华史》的编写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要到北京前门饭店开会。我问系领导开什么会,系领导说不知道,猜测可能是关于修改教材的会议。于是我带了两个月的粮票就来北京了。1974年7月5日到8月7日,基本上天天都在开会,会议的名字是“法家著作注释规划出版工作座谈会”,由李琦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全国出版单位的总编辑或副总编辑,但谁都不知道是让我们来干什么的。会议结束后,科教组负责人之一薛玉山才宣布,叫我们来是办《历史研究》的。
当时《历史研究》没有主编,编辑部的支部书记是曹青阳,另外有一个领导小组,由我、宁可和王思治组成。因为我刚过50岁,年纪最大,是副教授,头衔又最高,就被指定为《历史研究》领导小组召集人。
我在《历史研究》主要管“批苏修”,组织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文章。让我管“批苏修”是因为当时我在复旦大学主持编写《沙俄侵华史》,书还没有编完就把我调过来了。这一时期余绳武、谭其骧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关于中苏边界的文章,都是我组织的。1975年9月初,《历史研究》移交给学部后,我就离开了。我在《历史研究》工作了一年,离开后不想回上海,就去了金冲及任副总编辑的文物出版社。其实我不懂文物,只是把那儿作为避风港罢了。现在还没有人详细写过《历史研究》的那段经过,我一直想把它写成一个回忆录,但我现在手抖得厉害,写不了了。
《历史研究》,全国只有一份,在学术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刊物,要发表学术性比较强的文章,即材料扎实、拿史实说话、经过真正深入研究的文章,而不是感想议论式的文章。即使要发议论,也要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础。
后记
在见到胡绳武先生之前,记者一直怀疑是否能成功采访一位年逾九十的老人。出乎意料的是,虽然他身体已呈龙钟之相,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才思敏捷、逻辑严密,两次连续三四个小时的访谈,均毫无倦意。在他起居室的床上,整齐摆放着一叠报刊和书籍。搁在最上面的,是一本《资治通鉴》。当谈到某个人、某个问题时,他都能从旁边的书架上或抽屉里准确拿出相关的报刊或书籍,其笃学不倦的精神,令人感佩。可以想象,在青年和壮年时期,他是以怎样的精力和状态投入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作为新中国史学发展的见证人,这位学术大家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无疑是当今学界的一场精神盛宴。